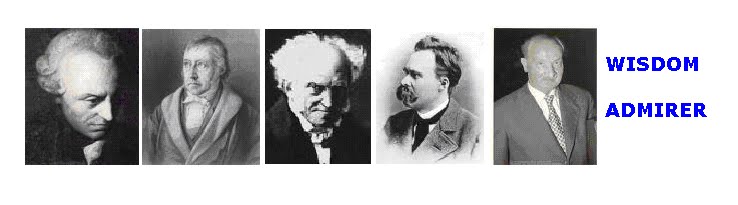第二天上午,潘乃穆到醫院的時候,原來負責治療的醫生已經靠邊站,新換的醫生態度惡劣,明知是危重病人,卻極力主張病人出院回家休養。乃穆說回家我們連灌腸都做不了,那位醫生也不予同情。潘光旦仍然堅持回家,他已經不能忍受這裏惡化的環境了,實際上醫生已經好幾天沒有給他治療了,也許他覺得與其這樣死在醫院,不如安安靜靜死在家裏。潘乃穆萬般的無奈,真有叫天天不應,叫地地不靈的感覺。在這種情況下,她給父親辦了出院手續。當時準備了一輛幼兒乘坐的竹制手推車把父親推出病房,潘光旦向很高興向旁邊不認識的人招手,如同病癒出院一般,而潘乃穆的心情更加沉重,她知道父親回家意味著什麼。
回到家裏,她先請求“監管人員”啟封,讓病人能睡到正常的床上,他們仍不准開啟臥室,只開了堂屋。她只好架起一張帆布床讓父親躺下。又偷偷地從門上的氣窗鑽進去,從裏面把必需的枕頭、被褥、衣物等扔了出來。那時,潘光旦病重成這個樣子,潘乃穆的單位又發生了問題,勒令她全新寫全部交代材料,她也不能留在父親身邊了。一天,民族學院通知北大生物系工作的潘光旦長女、在運動中備受衝擊的潘乃穟,說父親病重,准她半天假。乃穟於是見到父親這一面,這是“文革”以來唯一一次,也是最後的一次。
1967年6月10日晚上。。。
(待續)